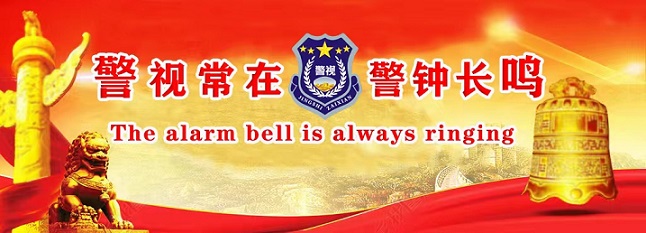
【基本案情】
刘某某在贵州省某市某区某乡集体土地上有两处房屋,一处面积为287.94平方米,并办理了相应的建房手续,另一处面积为1319.53平方米的房屋于2009年修建,但未办理任何建房手续。2016年8月,某区政府启动棚户区改造项目,并发布《安置补偿方案》,该方案规定对不符合建房条件的房屋(含外来户建房)根据不同修建年限给予一定的工料补偿。刘某某的两处房屋均在征收范围内,其中面积为287.94平方米的房屋按照合法建筑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并领取相应补偿金,面积为1319.53平方米的房屋因长期未达成补偿协议,于2019年8月15日被该区某乡政府强制拆除。刘某某对强拆行为不满,以乡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乡政府强拆行为违法,法院判决确认乡政府的强拆行为违法。刘某某后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乡政府赔偿强拆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以案涉房屋不是基于生产生活需要所建,且为违法建筑为由,只判决赔偿其室内物品损失2万元,对其他损失诉请未予支持。刘某某不服,提起上诉、申请再审均被驳回后,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某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关于赔偿的判决错误,遂向贵州省检察院提请抗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某某违法建设面积为1319.53平方米的房屋是否应予赔偿?如果赔偿,应如何认定赔偿金额?
针对上述问题,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受害人只有在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才有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刘某某于2009年修建的房屋,未办理任何建房手续,属于违法建筑,不应赔偿。且刘某某除了案涉房屋外,还有一处面积为287.94平方米的房屋,该房屋已获得征收补偿并领取相应补偿金,已经能保障其生产生活需要。法院以案涉房屋不属于生产生活需要而修建且未取得合法建设许可为由,判决只对室内物品酌情赔偿2万元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正是持此种意见。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否基于生产生活需要并不是判断房屋是否应予赔偿的条件。虽然案涉房屋未按照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办理用地、规划手续,属于违法建筑,但房屋违法并不代表房屋被拆除后其建筑材料也违法,乡政府应当赔偿其强拆行为给刘某某造成的房屋建筑材料损失。此外,案涉房屋的征收方案(《安置补偿方案》)已明确,不符合建房条件的房屋(含外来户建房)根据房屋不同修建年限给予一定的补偿,根据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法院应当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标准,判决乡政府给予案涉房屋一定数额的赔偿金。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安置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应同种情况同种对待。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订)》规定,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土地方案(下称“征收方案”)的行为,是相关征收部门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安置、赔偿损失的依据。从法律性质来看,征收方案中确定的补偿标准,属于人民政府对被征收土地上房屋及相关附属设施予以补偿的承诺,该标准涉及众多的不特定对象,具有抽象性和普遍约束力,对外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被征收人对此享有信赖利益,应当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本案中,案涉房屋涉及的征收方案已经明确规定,不符合建房条件的房屋(含外来户建房)应给予一定标准的补偿,不受一户一宅的限制,且该补偿标准并没有被法院判决撤销,大部分村民已经按照这一标准获得补偿,该方案对所有被征收人都应当适用。
第二,行政赔偿类案件应坚持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违法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的各项合法财产的实际损失总和。在房屋征收过程中,由违法强拆引发的行政赔偿类案件,行政机关强拆被征收人房屋的行为已被确认违法的,被征收人的损失问题应通过将征收补偿程序转变为行政赔偿程序予以解决。同时,为了体现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惩罚性,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应按照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来确定行政赔偿标准和金额。本案中,案涉房屋所在项目的征收方案已明确:2008年12月1日以后修建的房屋,给予每平方米200元的工料补助。案涉房屋修建于2009年,属于2008年12月1日以后修建的房屋,应当依此补偿标准确定相应的赔偿金额。
第三,是否基于生产生活需要不应成为认定行政赔偿的条件。首先,赔偿法定原则、有利于当事人原则是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从法律规定来看,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未规定基于生产生活需要是判断被强拆房屋是否应予赔偿的条件,司法机关不应突破法律规定作出不利于案件当事人的裁判。其次,基于生产生活需要本身是一种主观判断,实践中,当事人之所以出现一户多宅,往往就是为解决生产生活需要。最后,农村一户多宅现象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比如解决遗产继承问题或儿女成家的住房问题等,不应将所有违反一户一宅规定的房屋全部纳入不予赔偿的范围,这样不利于实现公平公正和矛盾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第四,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损失应予以赔偿。退一步讲,刘某某即使不能按照征收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得到赔偿,也应获得一定的建筑材料损失赔偿。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该条款明确了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对象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虽然案涉建筑物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受法律保护。但法律并未对违法建筑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如何处置作出明确规定,亦未规定没收建筑材料,故违法建筑拆除后的建筑材料权利应当予以保护。本案中,行政机关在实施强拆行为的过程中,未作出任何行政行为便强拆案涉房屋,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自行拆除权”,剥夺了其合理拆除房屋并对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再利用的权利,存在程序违法。同时,行政机关在强拆过程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对拆除后的建筑材料尽到了合理拆除并及时移交的合理注意义务,故应当对建筑材料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处理结果:贵州省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与省高级法院行政庭召开沟通协调会,经协商后达成共识,决定按照两院会签的《关于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实施意见(试行)》,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由省高级法院制发司法建议、省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共同督促某区政府按照征收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落实案涉房屋的赔偿问题。
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制发后,某乡政府及时向某区政府报告,某区政府主动自我纠错,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同意给予刘某某赔偿金26万余元。刘某某向贵州省检察院提交了撤回监督的书面申请书,贵州省检察院对案件作出终结审查决定,案件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作者单位: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编辑:筱月
